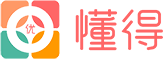世上真的有一辈子的情人吗?

世上只有忘不了的初恋,没有一辈子的情人,虽然自己没有过真正的情人,但是,和那些又是情人又不是情人的交往中,悟出了一种道理,男人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,女人没有漂亮的脸蛋,很难成为一辈子的情人。
所谓的情人,都是各有所需,男人贪色,女人贪钱,世间上,穷人永远不会有情人,只有那些生活无忧的人才拥有这种专利。
情人之间要有一定条件才能维持长久,如果男人情人节只给对方发100元红包,女人就会远你而去,如果女人只收红包,不愿付出,男人也不会无底线的在一棵树下吊死。
爱是一种付出,情人也是因为有爱才成为情人,所以,如果任何一方在交往中太过抠门,感情不投入,这样的情人不会长久,最终不欢而散。
一辈子的情人也许有,但相信很少,人的内心都有一种贪欲感,享受新鲜的欲望,所以,凡是愿意成为情人的人,他们的心里想法肯定不简单,而且想得很多,很复杂。
情人一开始交往都是美好的,双方也会感到很快乐,其间还享受到幸福的顶峰,可惜,随着新鲜感的慢慢退去,情人的好感也随着时间淡忘,最后只能作为一种记忆。
其实,人生有一个情人很快乐,但也很痛苦,快乐是因为两个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,痛苦是因为付出了代价,所以,一辈子有一个情人并不是什么好事,虽然女人无所谓。但男人肯定受不了,毕竟,维持一个情人的生活是要成本的。
没有情人想有情人,有了情人讨厌情人,这就是人生矛盾的关键点,因此,情人不需要长久,暂时即可。
世上真的有一辈子的情人吗?
我们单位就有一位,他是59年上海支援内地到我们单位的,我来时候他四十多岁,正巧住我隔壁,他人很风趣,生活很有条理,日常穿着整洁,为人谦逊,热情。这么好的一个人,却一直单身,时间长了,才发现一个中年妇女常到他这来,来时总挎个蓝子,上面盖个白毛巾,能猜到里面是做好的食物。那女人穿着朴素,却也很干净、整洁,头发梳理光洁,发型老式,后面一个发髻的那种。
时间长了,才渐渐了解了他的故事:他来时是单身,因为那女人来我院看病而认识,他一见钟情,可那女人己婚,并已生了一子,在他不懈的追求下,成了情人,那女人是家庭妇女,丈夫收入微薄,于是靠他的经济支持才勉强维持生济,后来丈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,选择了默认,所以他们维持了一辈子的畸形关系,他也一辈子没娶,算是个钟情汉,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住在医院,一直是那个女人服伺,直至逝世,也算是个善终。
世上真的有一辈子的情人吗?
我七姨和铁军,就是一辈子的情人。40年前,他们青梅竹马,经历各种风雨,不改初衷。
我七姨喜欢扭秧歌。正月初二姑娘回门子,姑娘姑爷一大家人,喝着茶水聊着天,如果有人提议说:“老七来一段儿。”七姨就爽快地说:“来就来!”
有人把地当间儿的八仙桌抬走,有人从柜子里找出扇子,丢给七姨。七姨接过扇子,“啪”地一个亮相,她的眼神就变了。邻居有会吹唢呐的。唢呐一响,七姨就扭起秧歌。她的每个动作都那么美,美到让你看不够。
姥爷不喜欢七姨扭秧歌,他说:“姑娘家家的,在男人面前,扭腰扔腿,以后还嫁不嫁人了?”
多年前,生产队给扭秧歌的人算工分。一入冬,七姨就参加秧歌队训练,正月十六才结束。菜农在冬天没地方赚钱,扭秧歌能挣工分,是不错的兼职。姥爷家是城郊的菜农,招工的事,那时候的规矩,都轮不到七姨。
七姨当时二十出头,漂亮,腰细。扭起秧歌来,那腰扭啊扭啊,我很担心她的细腰会折。那年冬天,七姨突然挎着一只红色的鼓回来了。鼓的中间细细的,像七姨的细腰。
七姨回来的时候,她身旁还走着一个男人,大高个,腿长胳膊长。那时候,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叫铁军。铁军和七姨走在一起,七姨脸上的笑容是带着温度的那种笑容,七姨的笑容能温热一杯冰水。
七姨回到家,自豪地对我们说:“这叫腰鼓。今年县里组办腰鼓队,让我当队长。”
七姨的腰鼓宝贝得不得了,谁摸都不让。吃完饭,她就把腰鼓斜跨在腰上,两手各拿一只筷子似的鼓槌,一边敲鼓一边扭秧歌。姥爷嫌鼓响闹人,不让她练。我妈就让七姨到我家去练。
我家在嫩江岸边,沿着江堤走过去,比走公路近一些。江上,渔火点点,镐头破冰的声音清脆悦耳。
马上要进腊月了,七姨训练忙起来。有一天她很晚还没回来,我带弟弟去接她。看见江堤上有个男的骑着自行车驮着七姨,就是那个长腿长胳膊的铁军。
我回家之后,就嘴快地对我妈说了铁军送我七姨回家的事儿。
晚上熄灯睡觉后,我听见我妈和七姨小声说话。 我妈说:“老七,送你回来的是谁啊?他叫铁军?铁军也是菜农?那你们俩岂不是一辈子都得种地?别跟铁军处了,让你姐夫给你找个工人,你也能到家属队当半个工人……”
一天晚上,我去接七姨,看到江堤上有人影。我走近才突然把手电筒打开。手电筒的强光照到两个人影挨得很近。那是七姨和铁军
七姨让我叫他铁军叔叔。铁军叔叔有点窘。在衣兜里摸出一块糖塞给我。冲我笑笑,他笑的样子很好看。
有一天,七姨跟我妈说她胳膊疼。我妈说可能是累的,歇两天。但两天后,七姨疼得更厉害了。她右胳肢窝下还摸到个包。我妈领七姨到医院检查,竟然是个瘤。
我妈带七姨去哈尔滨做手术。我二大爷家在哈尔滨。二大爷是很多年前,考上的哈尔滨商业学校,毕业后留在哈尔滨工作。家里有病人去哈尔滨看病,都住在二大爷家。
那年的春节,我妈和七姨都没回来,七姨在哈尔滨手术住院了。铁军不敢直接上门来找,等在江堤上。有天,我出去玩,铁军看到我,他才推着自行车走过来,问:“你七姨的病好点了吗?”
我说:“我妈带七姨去哈尔滨做手术。你去过哈尔滨吗?听我妈说,哈尔滨的冰灯挂一冬天。”
铁军又来过一次,是正月十五那天。傍晚,吃过炸元宵,我挑着小灯笼出门找伙伴玩,迎面看到江堤上有个人,手里提着灯笼走过来。他拎的灯笼是透明的,是冰灯!拎着冰灯的是铁军。
铁军把冰灯送给我了,还给我一封信,让我交给七姨。他走时回头冲我笑笑,说:“信,一定要交给你七姨。”
这封信,最后,却惹出一件大事——
过了二月二,我妈才带七姨回来。那时,铁军给我的冰灯都融化了。七姨没参加上腰鼓队的表演,她哭了。我姥姥拍着炕沿长吁短叹:“腰鼓就不应该练,别去外面疯了,找个对象嫁人吧……”
铁军的那封信,我给我妈了。为什么给我妈呢?因为那天七姨回姥姥家了,我翻开抽屉找糖纸,就看到这封信,我怕忘记了,就赶紧把铁军的信递给我妈。
我没想到,我的一个小小的举动,竟然酿成了一对情侣的分手。
第二天,我看见我妈把铁军的信交给了七姨。可七姨看完铁军的信,却躲在小屋里,眼睛都哭红了。铁军的信里写了什么,会让七姨哭成那样?我当时不知道,这封信,已经惹了祸。
当晚,我妈让我领她到江堤上等铁军。她说有话要跟铁军说。夜里江堤上很冷,我们走到江堤上时,铁军已经等在那里,似乎已经等了很久。帽子上都挂了霜。
我妈把手里的几张钱递给铁军。铁军不要,两人在江堤上推让着。
我妈说:“你的信,我交给老七了,信封里的钱老七让我还给你。”铁军说:“我把自行车卖了,就是给老七看病的,这钱给她买药买营养品吧。”
我妈说:“老七让我还给你,她说不能收你的钱。”我妈硬把钱塞给了铁军。铁军匆匆走了。江堤上他的影子被月亮拉得又长又瘦。我这才想起,他上次来就没骑自行车,原来自行车卖了。
我要是早知道信封里还赛了几张钱,我可能会偷偷抽出一张吧?铁军再也没来我家找七姨。我当时还不明白怎么回事。
后来,七姨处个对象,是个打鱼的男人。年底,七姨结婚了,打鱼的男人成了我七姨父。因为操办婚事,七姨没参加那年的腰鼓队。第二年七姨怀孕,第三年她怀了第二个孩子。那两年七姨的腰就没细过。
婚后,七姨就住在我家的西厢房。我妈很爱护七姨,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,就让我端一盘,送到七姨的屋子里。
那年,七姨怀了第三个孩子,我放学回家,经常看到七姨挺着大肚子在洗衣服。西厢房不大,床上趴着两个小孩在玩耍,墙上挂着七姨父的渔网。
一个冬天的傍晚,我放学回家,七姨让我回家拿点用过的草纸点炉子,我到我妈的炕柜里,掏出一些废纸拿给七姨。七姨要点火时,在废纸里突然挑出一封信。
没想到,这封信,又惹了祸。那是铁军那年正月里给七姨的信,我还记得。七姨不是看过了吗,当年她还哭红了眼睛。
整个下午,七姨一直拿着信,眼睛直勾勾的。后来,七姨让我给她看孩子,她挑着水桶出去了。天黑了,她也没回来。
我妈得知七姨去挑水,吓了一跳。我妈对我爸说:“老七那身子能挑水吗?你快去接她。”我爸披上军大衣就去井沿儿。七姨父打渔回来,把小木船拖上岸,也急忙去找,后来,我妈也去了。
七姨挑水时摔倒了。大出血,差点死在手术台上。隔两天,我妈点炉子,去炕柜里拿废纸,后来,她把我叫过去问话。她说:“你到我这里拿过废纸?”我说:“七姨点炉子没纸,她让我拿的。”
我妈指着炕柜里一只没锁的小木箱说:“你打开过这个箱子?是不是把一封信也拿走了?”我点点头。
我妈做饭时,对我爸说:“那封信的事儿,老七知道了。”我爸说:“当时把那封信烧掉就好了。”我妈说:“都怪爸,非要冒充铁军写信——”
七姨从医院回来,一直病着,脸色苍白,像个纸人。那些日子里,七姨住着的西厢房总是飘着汤药味。
七姨父每天去江上打渔。鱼打上来,用盆子装着。江边的鱼不论斤卖,论盆卖。七姨父总会留下一条鲫鱼给七姨熬汤。七姨瘦了,七姨父也瘦了。他用温毛巾给七姨擦脸,擦手,轻声跟七姨说话。
七姨父说:“我没别的能耐,我只会一辈子对你好。你就算不为了我,为了两个孩子,你跟我说句话吧……”
有一天,我放学回家,在江堤上看到铁军叔叔和我的七姨父站在一起。铁军叔叔好像老了,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帅了。
江风飒飒,他们没有听见我的脚步。我走近了,听见铁军说:“你天天去江上打鱼,现在打鱼的人多,鱼也少了,你要是累坏了,他们娘几个咋办?这些钱你拿着……”
七姨父说了什么,我没有听清,似乎是拒绝铁军的话。只见铁军把一只旧的挎包硬塞到七姨父手里,转身而去。七姨父手里托着那个旧的挎包,久久地矗立在树下。
当晚,我帮七姨父看两个小孩,七姨父在灶火上熬着粥,又在炉火上熬药。他一下子跌倒了,我叫了半天,他也没起来。
身后突然有人说话:“他该歇歇了,我来吧。”是七姨,站在我身后,七姨终于醒了,能下地干活了。
又过了十来年,七姨在一家工厂做零时工。那年,商业局正月要举办花灯会,有人知道七姨会扭秧歌,会打腰鼓,就让七姨组织腰鼓队。
那晚,七姨让我给她看孩子,她出去找人,组织腰鼓队。七姨的孩子毛毛和豆豆已经长大了。
那晚,七姨很久都没回来。我跟七姨父打着手电筒走过江堤去找七姨。江面上又开始破冰打渔了。有拖拉机从我们身边走过,车上都是做冰灯的冰。
在商业局的二楼,七姨正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,踩着鼓点儿打腰鼓。腰鼓打起来,七姨就变了,她还是十年前的七姨。
在大厅里打腰鼓的还有个男人,是铁军。他围着七姨打腰鼓,他扬起的脸还跟年轻时一样笑容灿烂。
七姨把红色的腰鼓背回来,擦得干干净净。我妈问过铁军的事。七姨说,这些年,他去南方打工,现在回来了,他一直没结婚。
七姨父依然去江面上凿冰打渔,他依然每晚拿回鲫鱼给七姨熬汤。但他话少了。紧接着发生一件不幸的事,七姨父从大坝上摔下去,摔折了腿。
有天傍晚,外面下雪了。我去柴垛拿柴禾,路过西厢房,听见七姨父的说话声:“我不能再照顾你,你跟他好吧,我们离婚吧——”
那晚的雪下得很大。夜深人静时,院子里突然传来打腰鼓的声音。拉开窗帘,我把眼睛贴到挂霜的窗玻璃上向外看,我看见了我的七姨——
只见七姨正在雪地上打腰鼓,她的动作快极了,她好像和她的腰鼓融为了一体。鼓声时而激越,时而低沉,就像一个女人在低诉饮泣。
我爸想让我妈叫七姨回屋,我妈说:“让老七打腰鼓吧,这些年,也苦了她。”
西厢房里,后来还是四口人。七姨没走,腰鼓也不去练了。后来很多年,七姨再也没有打过腰鼓。
我妈工作的制鞋厂后来停工了,我妈就自己开始做鞋。七姨就跟我妈一起干活,赚了钱姐妹俩平分。几年的时间,我家的三间土房翻盖成红砖房。七姨也在嫩江湾上游买了两间砖房。
七姨父的腿伤了以后,他不能再打鱼了,就在家给七姨做饭,给孩子们做饭。七姨说,七姨父做的饭菜可好吃了。七姨的两个孩子都上学了,七姨的腰也不再细,变得有些臃肿。
铁军后来在市里开了一家超市,超市干得红红火火,他经常带着车出去进货。铁军一直没结婚,他是不是心里还想着我的七姨?
又过了几年,我结婚了。后来,我又恢复单身。我带着儿子离开小城,在异地生活了很多年。这些年,家乡的变化很大,嫩江湾岸边都盖起了高楼。我妈家和七姨家,都住上楼了。据说,铁军已经开了第四家超市。
后来,我妈和七姨做鞋的生意不兴旺了,人们开始穿流行的鞋。这时候,我爸也退休了,我妈和我爸就开个小商店。七姨则去各处打零工,但她绝不去铁军的超市打工。
我和我妈在电话里经常聊到七姨。七姨的大儿子毛毛进了铁军的超市做经理,七姨的小女儿豆豆上大学的学费,铁军叔叔帮了不少。
七姨和七姨父都不要铁军的钱,但铁军说:“我也没家没孩子,要这些钱有啥用?能帮帮你们,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”
七姨父请铁军到家里吃饭,请十次,铁军叔叔能来一次。他来了,也只是喝酒,也不看七姨。只有喝醉了,才会望一望七姨,然后,就转身走了。
最近十来年,小城过年时,又开始打腰鼓了。就是不过年,广场里也有人打腰鼓。七姨父给七姨买回一个红艳艳的腰鼓,他愿意看七姨打腰鼓,他说,老七打腰鼓,就是好看。但是,七姨不打腰鼓。是不是七姨一打起腰鼓,就会想起铁军呢?
前两年,七姨父过世了。整个葬礼,都是铁军叔叔帮着七姨和七姨的儿子毛毛去办理的。今年正月,我回了趟老家,在街上见到七姨,我见到的是打腰鼓的七姨。
七姨正带着腰鼓队在街上表演腰鼓。七姨的头发已经花白,可打腰鼓的七姨却还是年轻的,窈窕的,她的腰一如当年那么细。旁边打腰鼓的一位老爷子,那不是铁军叔叔吗?他围着七姨打腰鼓,就如同当年一样。
写在最后:
世上真的有一辈子的情人,铁军叔叔年轻时爱慕我的七姨,一直到老,他依然深爱着七姨。
铁军叔叔从来不去破坏七姨的家庭,却一直默默地帮助七姨。爱你,就是对你好。只要你过得好,他做什么都觉得值得。
七姨婚后不再跟铁军往来,七姨父过世,七姨才又开始打腰鼓,和铁军续上前缘。
我是素老三,喜欢我的文章,请帮忙点赞、评论。谢谢!
版权声明: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将及时删除。